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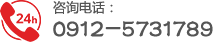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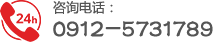
儿时关于杂面的记忆慢慢复苏了,母亲擀杂面的身影渐渐清晰起来……那时候,总觉得母亲擀杂面就像变魔术,一块圆圆的面团,一会儿变成一大张如纸一样薄薄的。一会儿又变成一根根长面条,眨眼间,长面条又一把把蜷缩在方方的盘子里,多神奇啊!母亲节俭能干,做的一手好饭菜,擀的杂面更是令人叫绝。在杂面就是“美味佳肴”的年代,要吃一顿杂面可没那么容易。记忆里,只有家里来了贵客,或是要招待匠人了,再不就是什么重要的日子,我们才能尝到母亲擀的杂面。那时候真是只有馋的份。一则东西缺少,再则家教严,家里无论是招待匠人或者是客人,母亲是不允许我们和人家坐在一起吃的,杂面煮出锅,我们就得到院子里去玩。等人家吃完,剩下的杂面才分给我们吃点。

印象最深的还是腊月二十三的那顿杂面。这天,母亲会早早起来,系上围裙,洗手舀面。两份白面,一份豌豆面,再捏上一小撮沙蒿面,搅拌均匀,就开始和面了。母亲和面自有一套,通常是左手倒水,右手和面,要把面粉打成穗子状,然后用手沾上水,一点一点往一块揉,直到揉成一大块面团。接下来要盖住饧面,饧上一阵后再揉,反复揉几次,直到把面揉的光滑Q弹。母亲说这样揉出来的面好擀,也好吃。杂面沾手,不好和,而母亲却是盆净、手净、面净。这和面“三净”也是母亲日后对我们和面的基本要求。要擀面了,大锅台上摆好案板,撒上一点面扑,(这是母亲专为擀杂面炒制的玉米面粉)。把面团放在案板上使劲揉几下,压成圆圆的薄饼型。这时我家那根长擀面杖就会隆重登场,母亲先是沿着面团的边缘往开擀,接着就会把面卷起来,两手轻轻托住擀杖两端擀,伴随着有节奏的“腾、腾、腾”,面团一圈圈变大变薄。一个回合结束,母亲总不忘把杂面抖开来,细细撒上面扑,卷起来再擀。不多时,一大张杂面就擀好了。令人叫绝的是那擀开的杂面,又大又薄又匀!别人都说杂面难做,和面难,擀面难,连切面也难,可在我母亲的手里却是那样的轻松娴熟,何来难做一说?比起擀面来,切面更是技术活。有的人切面粗细不均匀,有时还会连刀,煮出来也没人爱吃。母亲切面,刀刀下去细如线,匀若雨,又快又好。而且每切完一段,母亲都会顺手提面,轻轻抖落面粉,把杂面蜷在方盘上。动作连贯,一气呵成。更神奇的是母亲擀的每一把杂面,煮出来不多不少正好捞一碗。乡里的锅大,煮杂面要水宽些好煮。水烧开了,母亲总是先舀些开水浇在酸汤盆里,盆里早已放入葱丝、香菜、醋、盐等基本佐料,这叫调汤。杂面下锅之后稍微一搅,开锅即熟,这时候要赶紧用筷子捞面,有时怕溢出,还得往锅里点冷水。那杂面是越捞越长,一根头子不断,直到碗都盛不下还没捞断,得把胳膊举得高高的。看到母亲捞杂面,我有时候会开玩笑说:“这杂面要站在梯子上捞嘛,太长!”

我不光爱吃母亲擀的杂面,更爱吃母亲做的臊子。那些年乡里更是东西紧缺,做臊子也不见点荤,母亲总会想办法改善。有时她会弄两个鸡蛋,摊成鸡蛋饼,切成指头宽窄的条状,等素臊子临出锅时放入。刚出锅的臊子冒着热气,香味扑鼻,更不用说吃了。难怪我的大伯大妈从新疆回来,母亲给擀杂面吃,两人坐在老家的炕上,一会儿舀的喝口酸汤,说“香”,一会儿舀的吃一勺臊子,说:“好吃!”等到杂面捞上来,两人连臊子也不倒,直接浇上酸汤就开吃,还连声说着“好吃!香!”我们劝说舀上臊子吃,他俩会异口同声:“臊子味把杂面味压住了。”也是,食物最相思,大伯大妈几十年工作在外,这杂面,其实就是家乡的味道吧!如今,我也学会了擀杂面,虽然和母亲擀的杂面相差很远,但每一道工序我都不敢有丝毫的马虎。我知道,这擀杂面看似简单,其实特别讲究,必须用心去做。
每年的腊月二十三,我一定要自己动手擀杂面吃,因为这一根根杂面里有我儿时的记忆,更凝结着我们一家人浓浓的家乡情结。
